马元雄 :被异化者的自我救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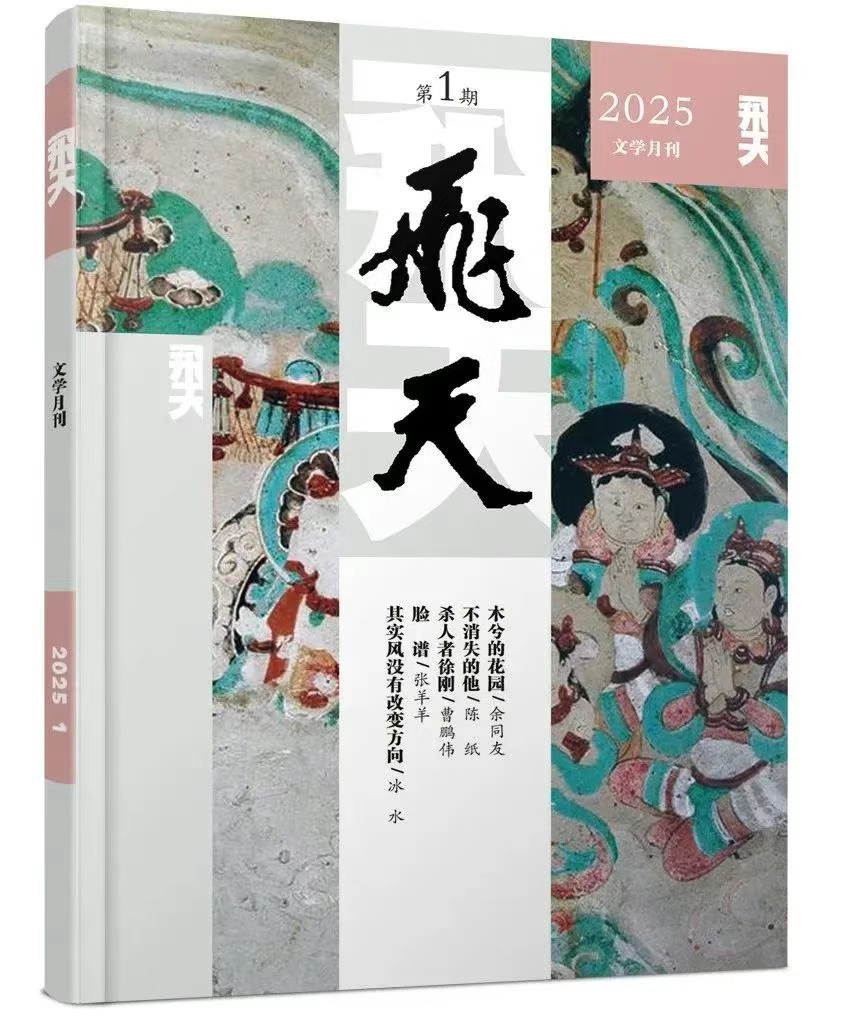
曹鹏伟的小说《杀人者徐刚》是一篇关注青春期成长问题的小说,在人物的刻画,结构的谋篇布局,语言的精炼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。叙述格局自然而开放,但蕴藏其中的精神却深邃沉郁,在作品中,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完美结合。作者极其注重文学的表现形式,叙述的角度和方法。写作是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,是以具体写抽象,以琐细的经验写精神的形状的,但这个写作的世界终归是从一个生活根系里长出来的,就像作者笔下的《杀人者徐刚》。
善用多角度叙事,语言暗喻性极强。标题醒目的为杀人者徐刚,初读让人为之一震,感觉徐刚凶悍、蛮横的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,但随着剧情的发展,层层抽丝剥茧,就像他那把刀,去掉刀鞘,其实是表兄箱子里最不起眼,也是最落寞的一把刀。板子高高举起,轻轻落下,由初始让人一惊与真诚、弱小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,巨大的反差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徐刚,骨子里的犹豫大于语言上的果敢,看似无所畏惧,其实只是发泄着虚无的怒火,想得太多,但行动得太少。“孟和镇人有秋冬吃狗肉的习惯。老中医说对气虚呀脾虚呀肾虚呀肺虚呀阳虚呀各种虚的人大有益处,补胃气,补虚劳,还能壮阳……”,精神空虚的时代,许多人和物似壮实虚,在貌似强大,实则虚妄的对立中互相捯饬,拉扯。但即使他们的力量弱小,面对外界的威胁和欺凌,所幸并未彻底屈服,仍努力抗争。“三个大人非常恼恨地指责我说,叫你说重点说重点……”,所谓的重点就是徐刚各种傻子般行为的行动依据和痛苦的根源,“我说,这些都是重点……”,看似繁琐的唠叨,其实是不断解套的过程,为读者解套,在精心的设套、解套叙述中将徐刚与余芳华狗扯羊皮的操蛋爱情故事交代清楚。全文最后,徐刚努力迈出了治疗创伤的一步,用冲动和热血展示了自己的倔强,明知自我的渺小,还是直面现实、正视对手,努力地完成了形体上和精神上的救赎,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。
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和反思。曹鹏伟的写作题材广泛,其小说擅于多角度、多元化、多种技巧的尝试,本篇聚焦于青春问题,直面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爱与痛,既是他本人的一次突破性尝试,也是对成长之痛这一经久问题的审视。在眼下校园霸凌、校内校外各种压力的时代背景下,徐刚和余芳华的早恋问题,被二鬼的欺凌等问题屡见不鲜,但对问题的直面要好于遮掩。“我”是亲历者,也是一个叙述者,有时客观冷静,有时“自嘲絮叨”,但总体来说理性多于诗意,理智多于感情,对事件人物的评价中肯合理,符合人物身份的讲述,让故事的内涵更加丰盈。“我俩卷起了裤腿,把鞋子顶在头上,像是两个投降的小兵。”两个小兵在伤害和互相伤害中经历着青春期的阵痛,他们面临着成长中的敌人。二鬼是徐刚直接面对的敌人,抢走了他的爱情,余芳华本应是他的盟友,两人曾一起私奔,然而这个准备长相厮守的另一半却背叛了他,应该说这是对杀人者徐刚的完美反杀,堡垒从内部被攻克。而“我”和徐刚,两个死党,在相互埋怨、角力中向着目标中的敌人发起冲击,所有的细节通过我这个“亲历者”和“讲述者”的双重视角展开。“我”既置身其中,又置身事外,相比于徐刚情感和心理的双重折磨,“我”更像是在割裂中行走在钢丝绳上战战兢兢地维系着平衡,自渡渡人,正是有了“我”的在场,让自我救赎才显得真实彻底且让人回味。当然此种阐释,太强的问题意识导向,即关于青春期的成长问题,难以回避小说所呈现的难题,想帮主要人物徐刚说话,其实更多的是“我”的理想性话语。
以狗为意象隐喻现实生活,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和面对现实无奈的自嘲。作者着力强调了成长必然具有的妥协含义,强调了成长与爱情之间复杂的纠结关系。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,看似不学无术、浑浑噩噩的徐刚和我浪漫的青春幻想,与二鬼、余芳华世俗的生活观、情感观抵触摩擦,而所谓的成长,只是向世俗化的庸俗欲望享受低头和退让。徐刚一句:二鬼把余芳华害惨啦!写出了他的心痛与无奈,殊不知人家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。当青春的浪漫幻想遇上机械化的生活欲望,成长因此变得沉重而难过。两个少年的成长理想遭遇来自家长的打压,来自爱恋对象的背叛,来自强大恶势力的欺凌时,他们努力抵制被外部世界“规训”和“同化”。“做狗不快乐,跟做人有啥区别?”“我不能活得不如狗”,此种对于人物的讽刺性呈现,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两个少年面对现实的无力感,但又做着力所能及的挣扎,内心的信念几近崩塌之时,他们激情追逐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只能通过救赎“更弱者”——一条待宰的小狗来完成。在小狗获得救赎时,徐刚也与过往和解,对伤害者宽恕,重建自我达到了创伤治疗、自我救赎。
“我”看似一个暧昧模糊的形象,实则是一个青春期的具象反映,是回忆昨日的起点和根据。在懵懂的青春期,很多男孩子都是“我”这般仗义的存在,为徐刚这样的“问题少年”两肋插刀,和他称兄道弟,为其出谋划策。徐刚和“我”以少年式的一元单纯性,遭遇班主任、家长和二鬼他们二元式的武断式和世俗性,是关联着这篇小说最基本的“成长”经验。直到最后,“我俩”虽已开始领悟到社会的“复杂”与“血腥”,但还是未妥协于他们的生存方式,而是刀不沾血的以自己的方式为小狗赢得一条出路,完成困苦的救赎,他们面对强大的“他者”做出了最微弱地抵抗,也是面对困境时的自我安慰、自我解脱、自我释怀。
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主题。伤害不是外在于自己的抽象主题,同时被内化为自己切身的伤痛。狗在二鬼这里接受了形体上的侮辱和毁灭,而“我”和徐刚不仅受到了身体上的殴打与羞辱,更是在精神上被对方凌辱。徐刚面临的“创伤”是多重的,渐次递进的,父母、老师加于他们的是言语的侮辱伤害,二鬼、葵花头施加于他们是身体上的殴打欺凌,余芳华给予徐刚的却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伤害,相比于徐刚挥出的那把丑陋的刀子,这才是致命的一刀,深深地命中一个懵懂少年的要害,将他的尊严和情感撕扯得惨不忍睹。狗是全文的一个绕不开的影子,所有的问题都会指向一个无辜且悲伤的存在,就是狗。“最后徐刚和我被扔在地上,像两条死狗一样趴在树下。”事实证明,在杀狗专家二鬼面前,我这条细狗和徐刚这条舔狗根本就不堪一击,被牢牢地拿捏,二鬼和他的狗腿子们收拾“我俩”就和收拾狗们一样,这是“我俩”的悲伤,也是狗们的悲伤。
过程的张力十足与结果的落寞反差,凸显“寻根者”的可笑。徐刚和余芳华失衡的爱情,从徐刚跋山涉水,冒险趟过鲁公河来找她,而对方只是用那一双分得很开的眼睛再三确认后,才冷冰冰地看向二人。再到后来的徐刚大张旗鼓的寻刀复仇,却发现自己只是个可怜的备胎,所谓的私奔只是人家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,“徐刚死猪不怕开水烫,余芳华还是皮薄一点,有点像伙同犯罪的推诿同伙求得减刑。”过程越激烈愈发衬托出结果的讽刺。我和徐刚一样,都经历过失恋,可谓是同病相怜,我的失恋过程虽未做交代,但徐刚的恋爱明显是剃头担子——一头热,被余芳华设计了,用时下话来说近似接盘侠,这就更凸显了他的荒诞与可笑,“回程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座隐于水下的水过面桥,那里距离我们抢滩登陆的地方仅一公里之遥。”抢滩成功后回去才发现有一座桥,就更影射了二人担惊受怕、苦心孤诣的渡河的可悲,原来自己做的都是无用功。
对场景细节的描写不遗余力,总是将细节与思考镶嵌其中,而不是简单平白地陈述一个事实,读后有酣畅淋漓之感。作者富有耐心且长久地凝视着一些细节,给予他们充分的观察,最终让他们成为思想的结晶体。如对杀狗的描写很有筋道,富有内涵,“它不想抵抗,只想用屁股瓷实地吸附住黄土地……它不得不跨开双腿,喇叭着屁股朝后退,在焦渴的地上划拉出一道道白线,嘴巴里呜呜着发出语气助词般的呻唤。”一吸、一跨、一退,将一条小狗面临灭顶之灾时的形体挣扎与内心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不空发议论,而是在充分描写之后,适时地加入一句点评,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“可徐刚就是喜欢舔啊,他跟个狗子一样追着人家屁股跑……”。作为徐刚的拜把子兄弟,“我”对他了解自是很深,评价也是一语中的。对徐刚心理的困惑苦闷、恼怒无奈分析的十分到位,这些细节描写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现象观察细致入微,对艺术描写的细腻入心。
从事文学的人,灵魂要生动,要发现普通人未发现的美,并将这种美记录并传播给更多的人。小说的结尾,落地的刀子是一种成长的隐喻。曾经所有的不甘、愤懑、冲动,在现实与精神的双重规训之下消弭于无形,杀人毕竟不同于杀狗,将承担法律责任,更要受到公德良俗的谴责,徐刚扔下刀子既是和对方的和解,放下了对方横刀夺爱的仇恨,更是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,以刀子入鞘的决心放下心中所爱。小狗就是我和徐刚的影子,解救它恰似解救了自己,小狗在赴死的路上被解救,而两个青春冲动的少年拿着刀子在作死的路上果断停下了脚步。生活的过程恰似趟过鲁公河,经过小马过河般摸爬滚打登岸,回头望来时路,发现路途并非想的那样艰难,所有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。或许,随着成长徐刚会发现,余芳华只是懵懂时期的一个驿站,这一切都很快将隐入尘烟。
——全文首发于《飞天》2025年第1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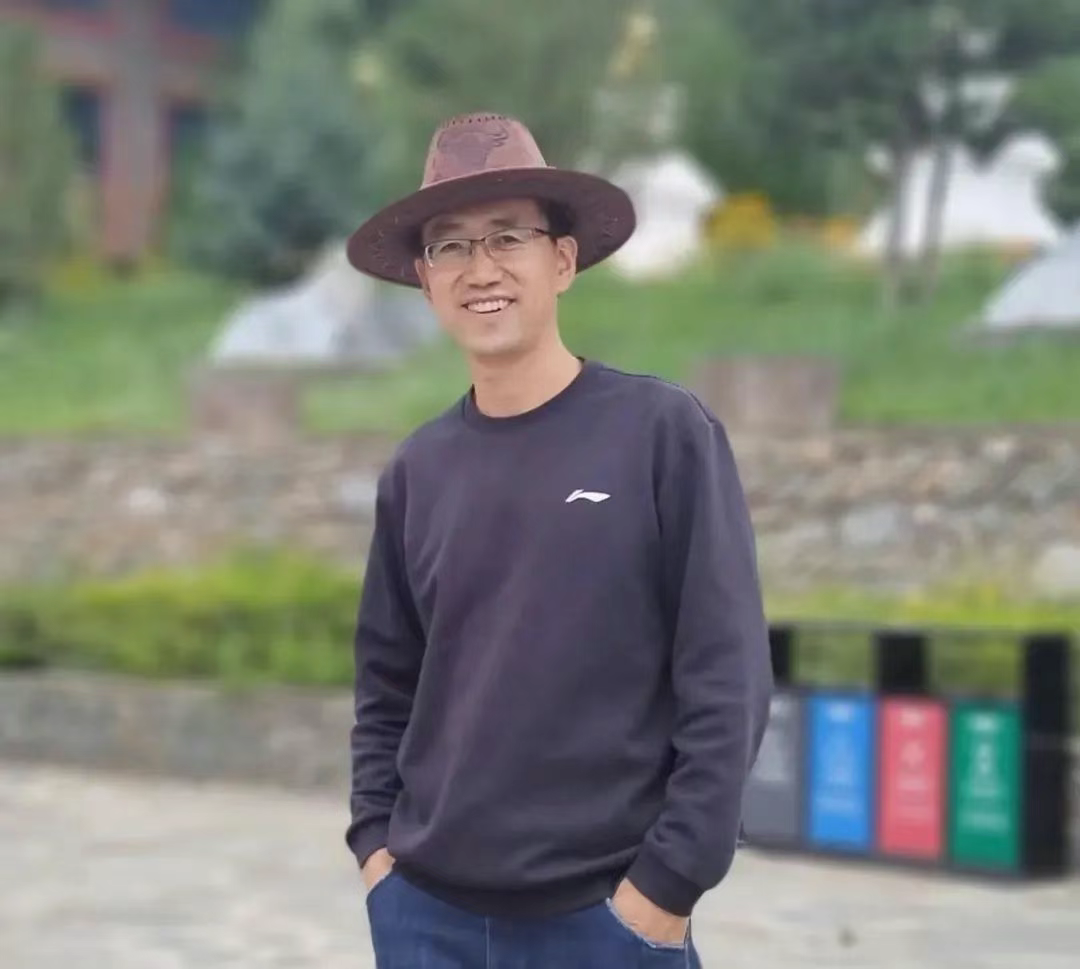
来源:飞天文学月刊






